作者:陈亚萍 李立润

本案是一起微生物发明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本案的案号是(2020)最高法知民终1602号,涉案专利是6012号专利,专利名称是“纯白色真姬菇菌株”,专利权人为F公司。涉案权利要求为“一种纯白色真姬菇菌株Finc-W-247,其保藏编号是CCTCC NO:M2012378”。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通过生物保藏编号对保护范围进行限定。
2017年5月23日,F公司委托代理人与公证处公证人员前往北京新发地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公证购买涉案产品,并对涉案的菌类产品进行了分拣、封存。涉案产品外包装箱上印制有H公司的商标,贴有L公司的封条,产品内袋印制有H公司商标并标注有L公司名称。
F公司遂向原审法院起诉H公司和L公司,原审法院于2017年6月22日立案受理。F公司要求判令L公司和H公司立即停止制造、销售专利侵权产品,销毁库存的专利侵权产品;判令L公司和H公司各向F公司赔偿500万元,合理维权开支30万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在本案中,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界定以及不同菌株之间的鉴定标准和方法成为主要争议焦点。
2019年3月22日,F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被诉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进行司法鉴定。
关于鉴定方法,F公司认为应当针对涉案专利与被诉侵权产品的基因特异性片段进行鉴定、比较;L公司、H公司均认为应当针对涉案专利与被诉侵权产品的全基因序列进行鉴定、比较。
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及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决定,要求鉴定机构同时使用上述两种方法进行鉴定,同时指出,鉴定机构可以根据其专业认识自行决定使用上述两种鉴定方法之外的方法进行鉴定,但必须在鉴定报告中说明采用此鉴定方法的理由。各方当事人对上述决定均无异议。
2019年6月26日,原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一同前往新发地中央批发市场购买涉案产品,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取出其中的2包涉案产品作为检材,经原审法院封存后,送往北京国创鼎诚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
北京国创鼎诚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2月12日出具的第163号鉴定意见记载:“北京国创鼎诚司法鉴定所根据原审法院提出的鉴定事项和涉及的技术领域,确定由程池、张海江、游涛三名鉴定人组成鉴定组。”关于鉴定和检验方法,第163号鉴定意见记载:“根据鉴定事项,我所委托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又名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该鉴定相关检测。为了保证检测顺利进行,经与委托方沟通后,我所鉴定专家组会同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于2019年9月3日与F公司沟通菌丝培养条件等技术问题,在沟通过程中,F公司告知涉案真姬菇具有双细胞核,需要先进行分核操作使其单核化才能进行基因序列检测,随后F公司提供了具体操作过程文件。根据F公司提供的分核操作方法及文件,鉴定专家组与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经过多次沟通,认为无法进行该分核操作,具体理由如下:1.分核方法不属于国标、行标等标准方法,也不属于经CMA、CNAS认证的检测项目,不属于常规的检测方法,因此通过该方法获得的数据和检测报告不能得到CMA、CNAS认证许可;2.由于该分核方法具有实验性质,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未进行过分核操作,无法预知实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无法确定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因此无法确定分核后的基因测序结果的可靠性。此外,鉴定专家组认为,由于纯白色真姬菇的性状、基因序列和所述特异片段来源的特点,根据涉案专利所述纯白色真姬菇的特异性975bpDNA片段的基因测序和比对结果可以判断出H牌白玉菇是否与涉案专利所要求保护的纯白色真姬菇属于同种菌株。因此,我所仅委托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进行委托方建议的第2种方法即按照涉案专利实施例12(即授权文本第118-123段)载明的方法对检材的特异性975bpDNA片段进行检测,同时根据鉴定需要对检材的ITSrDNA序列进行检测,据此结果开展鉴定工作。”
关于涉案专利要求保护的纯白色真姬菇和被诉侵权产品的对比分析,第163号鉴定意见记载:1.根据ITSrDNA序列检测结果,二者的ITSrDNA序列均与斑玉蕈HypsizygusmarmoreusHMB1(HM561968)的ITSrDNA序列相似度达到99.9%,因此,两者均属于斑玉蕈(另有汉语译名为蟹味菇、真姬菇、海鲜菇、白玉菇);2.根据特异性975bpDNA片段序列比对,二者特异性975bpDNA片段第1位至第975位序列完全相同;3.根据形态学比对,二者菌盖、菌褶和菌柄的颜色、形状、排列等形态特征基本相同。根据上述比对情况,鉴定组认为,二者属于同种菌株。
基于上述鉴定结果,L公司和H公司主张,第163号鉴定意见只鉴定出二者属于同种菌株,未鉴定出二者属于同一菌株,故被诉侵权产品未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原审法院认为,虽然第163号鉴定意见最终鉴定结论表述为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属于“同种菌株”,但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种”并非生物分类学中“门纲目科属种”中“种”的概念。因为若只是判断二者是否属于“同种”微生物,则仅需要形态学比对即可得出结论。而第163号鉴定意见除了进行形态学的比对之外,还对二者进行了ITSrDNA序列检测和特异性片段序列比对,显然这样的检测比对已经大大超出判断二者是否属于“同种”微生物的要求。因此,第163号鉴定意见所述“同种菌株”中的“种”是“种类”的含义,即指二者为同一种菌株。在原审庭审中,代表北京国创鼎诚司法鉴定所出庭的鉴定组成员程池也在庭审中明确,第163号鉴定意见结论中记载的“同种菌株”是指同一种菌株。因此,L公司和H公司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根据该鉴定意见的结论,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保藏的样本属于同一种菌株,故被诉侵权产品已经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此后,L公司和H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且,L公司二审期间还提交了新的证据,针对前述“同种菌株”的争议焦点,L公司提交了证据3-5拟证明全基因组序列测序具有可行性,以及原审通过ITS序列作为分子标记进行鉴定的方法不科学。(具体包括,证据3:云南农业大学官方网站登载的“我校科研团队公布90种野生菌全基因组序列”报道文章,拟证明云南农业大学2018年公布了90种野生菌全基因组序列,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对涉案白玉菇产品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是完全可行的。证据4:知网数据库《ITS序列分析在真菌分类鉴定中的应用》论文,拟证明以ITS序列作为分子标记,在属间关系鉴定上有价值,但不适合属内种及种群的鉴定,因此原审鉴定方法不科学。证据5:IPRdaily微信公众号文章“首例微生物专利侵权案件的分析和探讨”,拟证明仅仅通过两株菌具有相同的975bp的ITSrDNA序列,且根据形态学对比结果相同就推断出两株菌“属于同一种菌种”违背了生物学常识。)
关于被诉侵权产品与专利权利要求1的菌株是否为同一种真姬菇,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认为,由于本领域公知,SCAR分子标记技术是在RAPD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结果不受外界环境因素和生长发育阶段的影响,直接反映被鉴定菌株的遗传本质。SCAR分子标记可以通过获得某个菌株的“株特异性”标记来实现菌株的鉴定。本案中,涉案专利说明书明确记载了与市场上主要栽培品种并且是亲本之一的白玉菇H-W,市场购买的真姬菇G-W以及日本葛城新育成的白玉菇GC-W菌株相比,所述保藏菌株具有特有的SCAR分子标记975bp片段。因此,利用该菌株特异性975bp片段为检测指标,并结合形态学以及ITS序列分析对被诉侵权菌株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不局限于分类学意义上的“同种”菌株。因此,可以判断鉴定结论的“同种”不是分类学意义的“种”,而是同一种类的含义。虽然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书中没有对所涉菌株作出明确限定,但是微生物领域只需要有保藏号,通过保藏号保持菌株能获得DNA指令即可。由于另有分支标记专利对鉴定方法进行保护,涉案专利说明书记载的鉴定方法没有必要写入权利要求书中。因此,用涉案专利说明书记载的鉴定方法对被诉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进行鉴定,并未超出对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的微生物品种的解释范围。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并无不当。
关于通过检测975bp片段判断被诉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权利要求范围的鉴定方法是否合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认为,涉案专利说明书记载了保藏菌株Finc-W-247(CCTCC NO:M2012378)是通过亲本TNN-11和H-W杂交,再经系统选育获得。说明书详细记载了该菌株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和遗传学特性,还记载了该菌株的ITS序列结构,通过ITS序列结构构建菌株的系统发育树,所述保藏菌株为玉蕈属真姬菇。结合RAPD技术和SCAR分子标记技术,确认采用特异性引物可以从保藏菌株中扩增获得975bp片段,而在其他三株白色真姬菇H-W、G-W和GC-W中无法扩增获得该片段,故确认所述975bp片段为专利菌株的SCAR分子标记。通常,菇的生长繁殖主要分为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两个阶段,所述无性生殖主要靠菌丝在培养基上生长,有性生殖阶段可见明显菇体,在整个生长繁殖过程中,会形成单核的有性孢子和无性孢子,形成双核的菌丝、子实体,以及双细胞核融合形成双倍体细胞核的接合子。由此可见,对于常规菇类,其生长繁殖过程伴随不同细胞核状态,真姬菇的菌丝和子实体也具有双细胞核,而分核方法不属于国标、行标等标准方法,也不属于经CMA、CNAS认证的检测项目,不属于常规的检测方法,因此通过该方法获得的数据和检测报告不能得到CMA、CNAS认证许可;由于该分核方法具有实验性质,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未进行过分核操作,无法预知实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无法确定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因此无法确定分核后的基因测序结果的可靠性。在此情况下,鉴定机构寻求和选择本领域广泛认可的菌株鉴定方法是适宜和有必要的。由于本领域公知,SCAR分子标记技术是在RAPD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结果不受外界环境因素和生长发育阶段的影响,直接反映被鉴定菌株的遗传本质。SCAR分子标记可以通过获得某个菌株的“株特异性”标记来实现菌株的鉴定。本案中,涉案专利说明书明确记载了与市场上主要栽培品种并且是亲本之一的白玉菇H-W,市场购买的真姬菇G-W、以及日本葛城新育成的白玉菇GC-W菌株相比,所述保藏菌株具有特有的SCAR分子标记975bp片段。因此,利用该菌株特异性975bp片段,并结合形态学以及ITS序列分析对被诉侵权菌株进行鉴定的方法是合理且可信的。
关于仅采用975bp片段对菌株进行鉴定是否扩大了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的问题。根据前述描述,由于已经证明SCAR分子标记975bp片段是涉案专利保藏菌株的特异性标记,其他同种不同株的菌株并不含有该特异性片段,因此,以该SCAR分子标记作为检测指标,并结合形态学以及ITS序列分析可以反映待测菌株与专利保藏菌株是否相同,该判断方法并没有扩大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关于L公司和H公司主张涉案专利没有充分论证975bp片段是该菌株的特异性片段,原审中提交的证据表明全国各地多家企业的白玉菇以及韩国某白色真姬菇均含有975bp片段的问题。由于涉案专利说明书中已经针对保藏菌株与其他同种不同株的真姬菇进行了RAPD和SCAR分子标记分析,并提供实验数据(参见附图7)证明975bp片段是保藏菌株所特有的,L公司和H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专利说明书的实验结果有误,或提供证据证明在涉案专利申请日前,其他不同于保藏菌株的真姬菇也包含所述975bp片段,或者经过检索发现了其他真姬菇的基因序列中含有所述975bp片段,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涉案专利说明书的数据不真实有效。而对于全国存在多家企业以及韩国某白玉菇包含所述975bp片段的情况,由于不能证明这些白玉菇是涉案专利申请日前就在市场存在的,因此,也不能证明涉案专利说明书不是真实有效的。
综上,最高院认为,原审法院关于被诉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的认定正确。

关于被诉侵权菌株是否落入以“保藏号”限定的微生物发明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一般可以借助一种或者多种基因特异性片段检测方法,并结合形态学分析等予以认定。检测微生物菌株的基因特异性时,并非必须采用全基因序列检测方法,如果以“保藏号”限定的菌株具有特有特定序列扩增标记(SCAR)的分子标记片段,则可以该分子标记为检测指标,结合基因序列以及形态学分析,对被诉侵权菌株作出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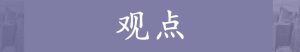
关于权利要求的解释通常包括三大原则,即周边限定主义原则、中心限定主义原则以及折中原则。周边限定理论的观点认为:应当对权利要求书中的文字表述作严格、忠实的解释;中心限定论则认为: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可以权利要求书记载的技术方案为中心,专利申请人只要确保该权利要求的内容能够反映其发明点或技术贡献,以满足授权条件即可;我国对于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解释则采取第三种原则,即折中主义原则,该原则最早起源于《欧洲专利公约》第69条及其议定书的相关规定,折中主义的内涵为: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根据权利要求的内容来确定,说明书和附图可以用来解释权利要求[1]。
在本案中,通过“保藏号”进行限定的微生物发明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原审法院和最高院均采用了“折中主义原则”对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进行解释。即,“保藏号”进行限定的微生物发明专利权利要求,其说明书中记载的相关形态学特征、基因特异性片段可以对通过“保藏号”进行限定的涉案权利要求进行进一步解释,进而明确涉案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这种解释方式在本案中显得相对合理,由于涉案专利的特殊情况,不具备通过全基因测序检测得出稳定、客观鉴定结果的条件,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记载的“形态学特征”以及“基因特异性片段”等内容对通过“保藏号”进行限定的微生物发明专利权利要求进行解释,明晰了微生物发明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合理保护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
至于拓展到它案是否可以不适用“全基因组序列一致”,在可以进行全基因组序列检测以确定是否侵权的专利侵权案件中,能否采用此种特异性基因片段检测方式确定侵权与否,本案的裁判要旨并未给出确切答案。
如果按照权利要求原始记载的书面内容理解,涉案专利仅仅保护具有与微生物保藏中心中的特定微生物具有相同全基因组序列的微生物。因特殊物种或鉴定技术等其他原因无法得出客观稳定的全基因组序列检测结果的,这种解释方式很可能导致专利保护制度形同虚设。再者,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对生物基因进行筛选甚至编辑的难度越来越低,侵权人如果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对基因进行修改,获得了与保藏中心保藏的微生物存在一两个无关紧要的基因位点差异的微生物,便规避了相应的专利保护,这显然极大地损害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对专利保护制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在此,笔者认为,其他通过保藏号限定的微生物权利要求,只要能够通过特异性基因片段和形态学特征确定是否为同一种微生物的,理应是能够借鉴本案的裁判要旨的。通过特异性基因片段和形态学特征综合进行侵权判定,而非硬性要求通过全基因组序列测序进行侵权判定,能够更加合理的对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这也是符合专利法的立法初衷的,有利于社会整体的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
执笔人:李立润,陈亚萍
责编负责人:陈亚萍,成员:李立润
案例来源:(2020)最高法知民终1602号民事判决书
参考文献:
[1]徐丹.保藏编号限定的微生物专利权保护范围探讨[J].中国科技信息,2022(18):21-23.
文章属性:原创
实务小知识:关于生物材料保藏规定
1、专利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10修订)
第二十四条 申请专利的发明涉及新的生物材料,该生物材料公众不能得到,并且对该生物材料的说明不足以使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实施其发明的,除应当符合专利法和本细则的有关规定外,申请人还应当办理下列手续:
(一)在申请日前或者最迟在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将该生物材料的样品提交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可的保藏单位保藏,并在申请时或者最迟自申请日起4个月内提交保藏单位出具的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期满未提交证明的,该样品视为未提交保藏;
(二)在申请文件中,提供有关该生物材料特征的资料;
(三)涉及生物材料样品保藏的专利申请应当在请求书和说明书中写明该生物材料的分类命名(注明拉丁文名称)、保藏该生物材料样品的单位名称、地址、保藏日期和保藏编号;申请时未写明的,应当自申请日起4个月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视为未提交保藏。
第二十五条 发明专利申请人依照本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保藏生物材料样品的,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需要将该专利申请所涉及的生物材料作为实验目的使用的,应当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请求,并写明下列事项:
(一)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地址;
(二)不向其他任何人提供该生物材料的保证;
(三)在授予专利权前,只作为实验目的使用的保证。
第一百零八条 申请人按照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对生物材料样品的保藏已作出说明的,视为已经满足了本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的要求。申请人应当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声明中指明记载生物材料样品保藏事项的文件以及在该文件中的具体记载位置。
申请人在原始提交的国际申请的说明书中已记载生物材料样品保藏事项,但是没有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声明中指明的,应当自进入日起4个月内补正。期满未补正的,该生物材料视为未提交保藏。
申请人自进入日起4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交生物材料样品保藏证明和存活证明的,视为在本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期限内提交。
2、关于中国实施《专利合作条约》的规定 第三十六条 指定中国或者选定中国的国际申请涉及新的微生物、微生物学方法或者其产品,而且使用的微生物是公众不能得到的,申请人最迟应当在国际申请日向专利局指定的保藏单位,或者,向依照《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藏布达佩斯条约》取得了“国际保藏单位”资格的保藏单位,提交微生物菌种保藏。在后一种情况下,申请人应当在本规定第十九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期限届满前,将该微生物菌种提交专利局指定的微生物菌种保藏单位保藏。
3、其他:我国关于专利程序的生物材料的保藏和提供样品的程序可参见《用于专利程序的生物材料保藏办法》相关规定,国际条约可参见《布达佩斯条约》(即《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