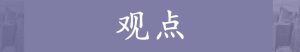本案是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件的再审案,案号是(2010)行提字第5号,涉案专利名称是“摩托车车轮(82451)”,专利号为200630110998.7。
图1 涉案专利立体图
图2 涉案专利后视图
涉案专利的相关设计特征如下:涉案专利为摩托车车轮,包括轮辋、辐条、轮毂三部分,其主视图显示其车轮外圈为圆形轮辋,内圈中心处为圆形轮毂,轮毂中心为轴承孔,轮毂表面分布近似五角形的加强筋,轮辋和轮毂之间均匀分布五根辐条,辐条整体呈逆时针旋转状,每根辐条两侧平直、表面光滑;后视图显示,辐条中间为凹槽状。左视图显示,轮毂宽度突出于轮辋。
无效请求人提供了某杂志底封上的摩托车车轮作为在先设计证据,二者主要不同之处在于:1、本专利有五根辐条,而在先设计为六根辐条;2、本专利辐条一面为平滑,另一面辐条表面有凹槽,而在先设计辐条表面为平滑和凹槽交替轮换;3、本专利与在先设计轮载表面的加强筋图案不同。
各方当事人对于前述事实并无异议,各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前述区别是否构成显著区别设计特征。在认定相关技术特征是否显著时,又涉及到关于涉案专利产品设计空间大小的认定问题,各方各执己见。
对此,最高院在该案判决中提出:设计空间是指设计者在创作特定产品外观设计时的自由度。设计者在特定产品领域中的设计自由度通常要受到现有设计、技术、法律以及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特定产品的设计空间的大小与认定该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对同类或者相近类产品外观设计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具有密切关联。对于设计空间极大的产品领域而言,由于设计者的创作自由度较高,该产品领域内的外观设计必然形式多样、风格迥异、异彩纷呈,该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就更不容易注意到比较细小的设计差别。相反,在设计空间受到很大限制的领域,由于创作自由度较小,该产品领域内的外观设计必然存在较多的相同或者相似之处,该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通常会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的较小区别。可见,设计空间对于确定相关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外观设计专利与在先设计相同或相近似的判断中,可以考虑设计空间或者说设计者的创作自由度,以便准确确定该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
在考虑设计空间这一因素时,应该认识到,设计空间的大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设计空间极大的产品领域和设计空间受到极大限制的产品领域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设计空间由大到小的过渡状态。同时,对于同一产品的设计空间而言,设计空间的大小也是可以变化的。随着现有设计增多、技术进步、法律变迁以及观念变化等,设计空间既可能由大变小,也可能由小变大。因此,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考量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空间,需要以专利申请日时的状态为准。
本案从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供的证据《摩托车技术》来看,即使摩托车车轮均由轮辋、辐条和轮毂组成,且受到设定功能限制的情况下,其辐条的设计只要符合受力平衡的要求,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存在较大的设计空间。
另外,关于“一般消费者”(即进行外观设计专利相同或相似判定的判断主体)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在该判决中还提出:《专利审查指南》(2006)中虽然规定一般消费者是一个抽象的人,但在具体的外观设计相同或相近似的判断时,必须结合所要判断的外观设计产品,需要将一般消费者这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与该产品相关的人群,而不可能如专利复审委员会在本案再审中所主张的那样完全进行抽象判断。
设计空间对于确定相关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外观设计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判断中,应该考虑设计空间或者说设计者的创作自由度,以便准确确定该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设计空间的大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可以变化的,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考量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空间,需要以专利申请日时的状态为准。
本案在争议焦点涉及“设计空间”案件中时常被引用,是国内较为详尽论述“设计空间”的司法实务判决,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本案中,明确了法院司法层面关于“一般消费者”的认定和关于“设计空间”的认定。
(一)关于“一般消费者”的认定
最高院认为,《专利审查指南》(2006)中虽然规定一般消费者是一个抽象的人,但在具体的外观设计相同或相近似的判断时,必须结合所要判断的外观设计产品,需要将一般消费者这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与该产品相关的人群,而不可能如专利复审委员会在本案再审中所主张的那样完全进行抽象判断。
即,在进行外观设计专利相同或近似认定时,需要根据《专利审查指南》将抽象的“一般消费者”的概念具象为与专利产品相关的具体人群进行相同或近似的认定。如本案中,可能接触到该车轮外观产品的人群就包括了“组装商、维修商、购买者和使用者”。
将抽象的“一般消费者”具象为与专利产品相关的人群是司法实践中的一般观点,不管是侵权认定还是授权确认阶段,法院都是倾向于此种观点,包括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20)摘要”中,也提到了“在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案件中,不同产品的消费群体可能会有所差异,故对于一般消费者的范围,应结合产品的实际购买、使用等情况具体确定”;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2)”中也提到“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通常包括在产品交易、使用过程中能够观察到或者会关注产品外观的人。如果产品的功能和用途决定了其只能被作为组装产品的部件使用,该组装产品的最终用户在正常使用组装产品的过程中无法观察到部件的外观设计,则一般消费者主要包括该部件的直接购买者、安装者”。
然而,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层面却持与法院司法层面不同的观点。参考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无效审理部官网文章“【十大案件】评析‘仪表机壳’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案”,其中提到“作为外观设计中的判断主体,‘一般消费者’是法律拟制的概念,其设定目的在于减少判断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影响,从而使判断结果更为客观并可预见。作为一种假设的人,我们不能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消费者相混淆,应区别于真实的个体或群体,其既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消费者,也不应将其简单地对应于某一类具体人群。作为判断主体应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其能力是由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的现有设计决定的,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即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层面,将“一般消费者”视为如同“本领域技术人员”的抽象概念,以此作为外观设计判断主体会使判断更加公允客观,一般消费者之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只与申请日前所有的现有设计相关,并且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对比前述两种观点,笔者更加倾向于认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观点。如何客观公允地评价发明创造的创新程度,一直是专利审查中的难题。“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法院所持的观点将“一般消费者”在司法实践中具象为具体的人群的做法,显然是为了实操方便,具象化后的一般消费者便于认定“某些设计特征对外观是否有显著影响、是否容易观察到”。但是,这种具象化的操作实际上是在尝试穷举可能存在的“一般消费者”人群,这种穷举方式容易导致分歧。例如,在本案(2010)行提字第5号中,一审法院认为“一般消费者”是维修商和组装商,普通摩托车购买者一般不会留意到组装在摩托车上的车轮设计,并且维修商和组装商对车轮外观设计的辨别能力应当高于一般消费者;二审法院又认为:对摩托车车轮外观设计的一般消费者应当包括组装商、维修商还包括普通的摩托车的一般使用者、消费者;最高院又认为:“一般消费者”这一抽象概念在具体案件中应当具象为具体的人群,本案的“一般消费者”应当包括组装商、维修商、使用者和购买者,不能认可专利复审委所提出的基于完全抽象的“一般消费者”进行相同或相似认定。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本案法院司法层面实际上就是在不断穷举“一般消费者”人群,不同审级对于“一般消费者”概念产生了明显的分歧,这种飘忽不定的“一般消费者”认定,影响了对“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认定,显然会影响对外观设计相同或相似的判断。不同阶段的产品使用者,明显具有不同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法院在穷举不同的“一般消费者”人群后,如何在不同的“一般消费者”人群中锚定其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显然是困难的。在“组装商、维修商”眼中,其能观察到的产品细节更多,诸如“轮毂”、“加强筋”等“一般使用者、购买者”日常使用不容易看到的设计细节,在“组装商、维修商”眼中均是容易观察到的。法院在进行设计特征是否显著影响整体设计外观时,显然是需要作出取舍的,这种取舍最终导致产生不同的外观设计相同或相似认定结果。相反,适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无效审理部的观点,直接统一认定“一般消费者”,对于“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锚定于专利申请日前所有现有设计常识的水平,这样能够使各方均站在统一的视角,对外观设计作出合理、公允的认定,避免了主观臆测外观设计创新程度以及一般消费者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以上仅为笔者之拙见,仅为观点讨论,不作为实务参考,各位还是应当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具体实务观点处理具体案件。
(二)关于“设计空间”的认定
首先,在侵权纠纷案件和授权确权案件中,二者关于设计空间认定的时间节点不同。
在授权确权案件中,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一般消费者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应当考虑申请日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设计空间”,即授权确权案件的设计空间认定时间节点为涉案专利的申请日。
而在侵权纠纷案件中,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认定一般消费者对于外观设计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时,一般应当考虑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授权外观设计所属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设计空间”,即侵权纠纷案件的设计空间认定时间节点为侵权行为发生时。
其次,关于设计空间的影响因素,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规定:
“对于前款所称设计空间的认定,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一) 产品的功能、用途;
(二) 现有设计的整体状况;
(三) 惯常设计;
(四)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五) 国家、行业技术标准;
(六) 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根据前述规定并结合本案的裁判要旨可知,设计空间是指设计者在创作特定产品外观设计时的自由度。设计者在特定产品领域中的设计自由度通常要受到现有设计、技术、法律以及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并且,设计空间的大小也是可以变化的。随着现有设计增多、技术进步、法律变迁以及观念变化等,设计空间既可能由大变小,也可能由小变大。设计空间较大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一般消费者通常不容易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的较小区别;设计空间较小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一般消费者通常更容易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的较小区别。
执笔人:李立润,陈亚萍
责编负责人:陈亚萍,成员:李立润
案例来源:(2010)行提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
参考文献:
[1] 蔡伟,欧群山. 浅析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断中的“设计空间”[N]. 人民法院报,2021-07-22(007).DOI:10.28650/n.cnki.nrmfy.2021.003481.
[2] 张爱国,常宝堂. 外观设计的设计空间[C]//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论文集.[出版者不详],2015:4.
[3] 程云华,【十大案件】评析“仪表机壳”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官网.
[4]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2),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官网.
[5] (2021)最高法知行终464号行政判决书.
文章属性:原创
实务小知识:外观设计的设计空间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16年3月21日,法释〔2016〕1号)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在认定一般消费者对于外观设计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时,一般应当考虑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授权外观设计所属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设计空间。设计空间较大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一般消费者通常不容易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的较小区别;设计空间较小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一般消费者通常更容易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的较小区别。
2.在考虑设计空间这一因素时,应该认识到,设计空间的大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设计空间极大或者设计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两种极端情形,设计空间对于外观设计近似性判断的影响较为凸显,但在此外的大多数外观设计侵权案件中,设计空间的作用实际上相对地被弱化,因此,在外观设计专利与被诉侵权设计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判断中,应当注意避免对设计空间适用的泛化。之所以规定设计空间,目的在于更加准确地确定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
参考:宋晓明、王闯、李剑:《〈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10期(总第7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