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亚萍 李立润
本案的案号是(2020)最高法知民终1848号,案件名称为Z公司与宋某某专利权权属纠纷案,存在权属纠纷的涉案专利专利号是ZL 201821872940.X,专利名称为“一种圆环形高温微波膨化炉”,申请日为2018年11月14日,申请人(专利权人)为宋某。
2018年4月23日宋某入职Z公司,从事设备维护和管理工作,根据Z公司所提交的会议纪要、宋某个人绩效评估和工作总结及日常工作情况汇报等记录显示,宋某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招标及采购、设备的安装调试和日常维护保养、传送带测试及与厂家交流、用采购的高温毡对输送带进行改造、厂区安全卫生保洁等。
Z公司为了实现石墨的连续微波膨化和石墨烯的产业化生产,2017年5月从株洲某公司购入一台100KW连续式微波石墨膨化设备。Z公司声称该设备系根据被授权的“一种微波膨爆制备石墨烯的方法”的发明专利向案外某公司定制,但未提交定制证据。
涉案专利与微波膨爆设备均属于石墨烯生产设备领域,均是为解决石墨的连续化微波膨化制备问题。郑州某公司提交的设备照片显示,其所购入并使用的微波膨化炉与涉案专利相比,相同之处在于:均设有进料腔和物料输入系统、微波输送导管和微波加热腔、气动吹料分布管、分离仓及出料腔等。主要区别在于,涉案专利采用腔体容置的圆环形转盘输送物料,在专利实施方式中描述,其圆环形转盘使用白刚玉面板;而郑州某公司购入并使用的微波膨化炉使用高温毡材质的皮带往复式输送带。宋某某确认,其研发涉案专利的动机源于在郑州某公司工作期间,郑州某公司的微波膨化炉输送带频繁烧坏,故在专利中使用“圆环形物料输送装置”代替皮带往复式输送带。
郑州某公司认为,对设备进行维护调试、升级改造是宋某某的本职工作,同时宋某某在入职之前并无相关教育经历或相关技术工作经验,系在郑州某公司工作期间接触并了解了石墨微波膨爆技术,其工作总结中也多次提到其工作内容包括石墨烯膨化设备的研发,故涉案专利研发属于宋某某的本职工作或履行单位交办的工作任务;同时涉案专利技术特质与公司设备基本一致,唯一区别“圆环形物料输送结构”是在使用和调试设备过程中针对设备出现的问题产生的设备改造方案,宋某某利用郑州某公司石墨微波膨爆设备、石墨原材料、微波炉、设备改造方案和设备实验数据等物质技术条件进行操作实验,应当认定主要利用了郑州某公司的物质技术条件。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涉案专利属职务发明,应归属郑州某公司所有。
宋某某则辩称,涉案专利是工作之余的发明创造,既不是本职工作也未履行工作任务;涉案专利没有利用郑州某公司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其技术与郑州某公司采购的设备使用的升级改造技术完全不同。
经二审法院查明,认为该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专利是否属于职务发明创造。
专利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前述规定将发明人履行本职工作或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外的工作任务、或是主要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认定为职务发明。履行本职工作或工作任务体现了单位的意志,主要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体现了单位的投入,两者共通之处在于单位生产要素对于发明创造起到了实质作用。
本案中,宋某和Z公司之间不存在关于对宋某工作期间发明创造权属的有效约定,故本案应从查明涉案专利与Z公司微波膨化炉技术方案的关系出发,审查宋某的工作任务或Z公司物质技术条件对于涉案专利的取得是否发挥了实质作用,以此判断Z公司是否具有取得涉案专利的合法依据。
(一)关于涉案专利与Z公司微波膨化炉技术方案的关系
涉案专利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确定,源于宋某在Z公司的工作内容。涉案专利与Z公司微波膨化炉技术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以圆环形转盘代替了皮带式输送带。这也是相对于在案证据所反映的现有技术而言,涉案专利的实质性特点所在。
(二)关于宋某的工作任务认定
尽管2018年10月18日Z公司的会议纪要显示,宋某被要求解决传送带寿命问题,但该次会议中宋某所汇报的工作内容是完成(输送带用)高温毡的采购、下周计划用高温毡对现有输送带进行改造。由此可知,宋某的工作任务仅限于在Z公司既有的皮带往复式输送带的技术方案范畴内更换高温毡材质输送带,而不包括提出新的技术方案来取代输送带。另一方面,Z公司在上诉中亦提出,宋某毫无石墨烯微波膨爆制备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宋某自2018年4月入职,至2018年11月申请专利仅相隔半年。故Z公司将研发任务交付宋某亦不合常理。同时,涉及涉案专利的成绩表述被纳入“挑战创新”工作板块,显著区别于Z公司确定的宋某本职工作内容;宋某在日常工作汇报中也未向Z公司报告研发进度或寻求公司帮助解决相关技术问题。故宋某成绩报告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宋某完成涉案发明创造系履行本职工作或者本职工作之外的工作任务。
(三)关于发明创造的物质技术条件认定
二审法院认为,物质技术条件可以具体划分为发明创造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在特定情形下,单一元素如设备可以兼具物质与技术条件属性。这其中,物质条件一般包括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等,其用途为直接或间接用于开展研发活动并在分析、验证、测试之后得到发明技术方案,包括在研发过程中对特定技术手段所产生的技术功能和效果或专利技术方案实用性等技术内容的分析、验证、测试,对于形成发明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而技术条件则指未公开的技术信息和资料,包括尚未公开的技术成果、阶段性技术成果等,对于形成发明的实质性特点具有技术启示。
就本案物质条件来看,Z公司并无用于涉案专利研发的专门资金投入,其石墨烯微波膨化炉的生产、调试、传送带用高温毡的采购和替换等物质条件的提供和消耗,一则并非因为宋某的意志而进行,而是在Z公司组织的生产测试过程中被消耗,Z公司并无为宋某的科研活动提供物质条件的意思表示;二则相关物质条件的消耗过程并未指向宋某的科研活动,涉案专利较现有技术改进的主要创新在于“圆环形物料输送结构”,Z公司的相关设备、零部件不包括“圆环形物料输送结构”,亦无物质条件因指向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研发过程中的分析、验证、测试而被使用,即未对发明的取得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故从物质条件的使用来说,Z公司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涉案专利的研发提供了主要物质条件。
就本案技术条件来看,Z公司提出宋某并无专业背景和从业经验、系接触到Z公司石墨烯微波膨化炉设备才产生发明创意、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的部分内容与该设备相同。二审法院认为,对于单位来说,其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属于单位的技术储备,对于单位来说具有潜在的无形财产价值。但应注意的是,不宜将发明人在涉案专利的发明创造过程中所处的技术环境或者所掌握的公司技术资料,与法律规定的技术条件相混淆。如果相关技术资料对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实质性特点不能提供技术启示,则原则上不应对专利权属产生影响。本案中,Z公司所使用的石墨烯微波膨化炉系自株洲某公司购入,Z公司并未有效证明该设备系Z公司提供技术方案、且技术方案未对外公开的事实,亦未证明宋某的发明创造使用了Z公司的设备改造方案和设备实验数据,故不足以认定Z公司为涉案专利的研发提供了主要技术条件。
此外,前述Z公司提及宋某的发明创意来源问题,实质主张系涉案专利技术问题的确定对专利权属具有影响。对此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厘清技术问题的性质和对发明技术方案的影响,区分个案情况予以判断。在技术问题属于单位阶段性技术成果且不为外界所知悉的情况下,该技术问题可使发明人避免陷入错误的研发方向,并因此缩短了研发进程,此时该技术问题可视为本单位的技术条件;而在技术问题属于公知或属于非为单位内部掌握且未被采取保密措施的外购产品技术缺陷的情况下,相关发明创造的技术问题则不构成本单位的技术条件,单位并无据此主张权利的依据。本案中,宋某虽系在对石墨烯微波膨化炉的生产、维护和改造过程中,获知该设备存在输送带开裂导致寿命短的技术问题,但如前所述,该技术问题产生于株洲某公司所生产的涉案设备,且至少被株洲某公司和Z公司同时所知,Z公司未举证证明此技术缺陷问题属于其不对外公开的技术信息,故Z公司据此对专利权所提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涉案专利的发明创造并非因Z公司向宋某交付工作任务而肇始,在研发过程中Z公司亦未向宋某提供专利法意义上的主要物质技术条件。涉案专利属于宋某在本职工作和单位交付的任务之外所完成的发明创造,Z公司对于涉案专利研发未投入人力物力、未储备相关技术资料、亦未预料其产生,发明人自身的智力劳动对于发明创造起到了决定作用。故应当认定涉案专利归属发明人宋某所有。
关于“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发明创造的认定中,“物质技术条件”包括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等物质条件和未公开的技术信息和资料等技术条件;“主要”是对前述物质技术条件在发明创造研发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限定,系指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是作出发明创造不可缺少的条件,相对于发明人使用的其他来源的物质技术条件而言,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在重要性上胜过其他来源的物质技术条件,居于主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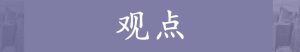
在本案中,其特殊的地方在于,一般的单位与发明人专利权或者专利申请权纠纷案件中,通常都是发明人离职后一年内作出的发明创造引发的纠纷,但这个案子中专利申请时间是发明人在职期间;同时,该项发明创造是针对单位所使用的机器设备所做出的进一步改进。在前述两个背景条件下,法院依然没有支持该项发明为职务发明。
在本案中,Z公司实际上为宋某研发涉案专利提供了接触到“技术问题”的便利,但是该技术问题并非Z公司独家掌握的内部技术秘密,在本案中至少有Z公司和案外人株洲某公司知晓,Z公司也无法证明该“技术问题”属于未公开的技术秘密。因此,在技术问题属于公知,且对于发明人解决相关技术问题无法起到实质性作用,如帮助发明人缩短研发进程、避免陷入错误研发路径等,因此该技术问题不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物质技术条件。
《专利法》第六条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该单位可以依法处置其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促进相关发明创造的实施和运用。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申请被批准后,该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为专利权人。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从上述法条可以看出,涉及职务发明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其一是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其二是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可以包括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以及退休、调离原单位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终止后1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在这种情况下,单位方一般持有项目开发文档、任务指派记录等与指派任务相关的证据材料,一般情况下较为容易认定相关的权利归属。
而“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的定义,比起“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的定义相对模糊,专利相关法律法规中也仅仅在《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做出了“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是指本单位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的解释。这对如何正确理解“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造成了一定困难。
经检索,在《民法典》第八百四十七条中规定了“职务技术成果”,是《专利法》所表达的“职务发明”的上位概念。对应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第四条对“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做出了具体规定,具体规定如下:“民法典第八百四十七条第二款所称“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包括职工在技术成果的研究开发过程中,全部或者大部分利用了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资金、设备、器材或者原材料等物质条件,并且这些物质条件对形成该技术成果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还包括该技术成果实质性内容是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尚未公开的技术成果、阶段性技术成果基础上完成的情形。但下列情况除外:(一)对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约定返还资金或者交纳使用费的;(二)在技术成果完成后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对技术方案进行验证、测试的”。
在前述司法解释中,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较为容易理解,即单位各种形式的公司资产,如公司的技术文档、设备、资金等。在该规定中,更加值得关注的关键点在于:(一)物质条件对形成该技术成果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二)该技术成果实质性内容是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尚未公开的技术成果、阶段性技术成果基础上完成的。也就是说,除了对单位的物质条件的使用外,单位的物质条件应当与发明创造的技术方案存在实质性关联,对形成发明的实质性特点、促进发明技术方案研发进程等具有实质性影响;或者说职务发明是基于单位所掌握的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进一步研发创造后取得的。当个人有偿使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或者仅仅在完成了技术成果后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进行测试、验证,此为职务发明的例外情况,单位无法因此获得相关专利权权属。
本案的意义在于,对“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这一法律概念做出了较为系统的探索,详细地论证了何种情况才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本案的潘才敏法官针对职务发明物质技术条件认定提出如下审查步骤方法:
(1)查明作为必要事实依据的发明技术方案;
(2)确定争议的技术内容与物质技术条件的对应关系;
(3)审查技术问题的发现是否构成技术条件;
(4)审查技术环境是否构成技术条件;
(5)从单位“可期待”、“可预期”角度的检视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物质技术条件。
责编负责人:陈亚萍,成员:李立润
案例来源:(2020)最高法知民终1848号民事判决书
参考文献:潘才敏.激励创新视角下的职务发明物质技术条件审查[J].法律适用,2023,No.491(02):113-123.
文章属性:原创
1、职务发明的判定由“任务标准”和“物质技术条件标准”构成。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处理职务发明纠纷案件时的普遍裁判逻辑为:由于“任务标准”的内涵较为明确,法院会优先适用“任务标准”进行判定,在判断案涉发明不满足“任务标准”后,再进一步通过证据判定是否符合“物质技术条件标准”。
2、“任务标准”指发明创造是发明人在执行本单位的任务,《专利法实施细则》和《解释》对这一标准的详细注释,在学界和审判实务中基本没有争议。
3、“物质技术条件标准”指发明创造是发明人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主要利用”应基于“全部或大部分利用”及“实质性影响”两个条件来判断,这就给司法实务审判留下了诸多解释空间。首先遵从约定优先。其次在无约定情况下,判定是否“主要利用”。在不能判定是“主要利用”还是“次要利用”时,可以通过分析发明与“本职工作”的关系来判断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的性质。最后在判定是“主要利用”情况下,再确定这些物质技术条件对形成该技术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如果由本单位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对发明不具有实质性影响,则发明不构成职务发明。
4、在对非本单位人员参与了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进行的发明的权属的判定中,在无合同关系约定的前提下,“物质技术条件标准”仍然适用。
参考文献:
[1]冯亚平,张健东.科技成果转化视域下职务发明的认定与适用研究——以某医院与其单位职工李某某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为例[J].法制博览,2022,No.891(31):151-153.
[2]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高民终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书,某医院与李某某专利权权属纠纷案。



